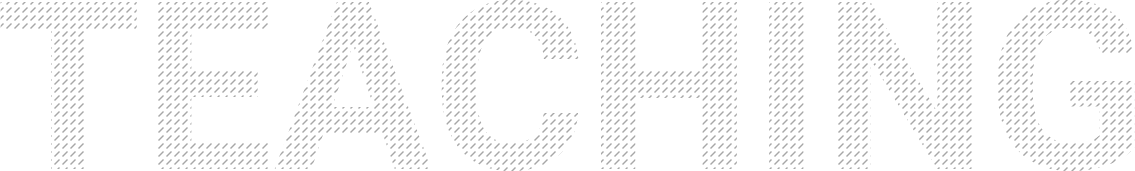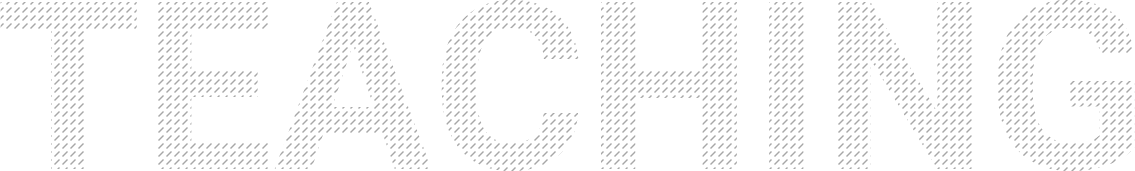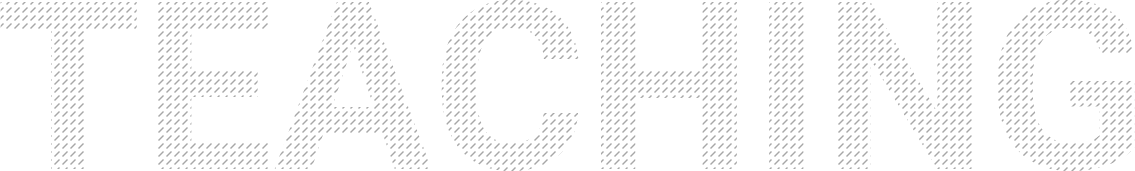2022年12月,2022首届物质文化与设计研究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评议结果公布,华体会网页版登录入口艺术史论系博士研究生周少华(指导教师:艺术史论系副教授 陈彦姝)论文《明代云南雕漆再考》荣获第一组工艺美术史研究一等奖。
《明代云南雕漆再考》
在明代雕漆产区中,云南当年可能地位重要,前辈学人曾提出,明代雕漆有两个地区系统,一是嘉兴,另一就是云南。可惜,因为文献史料稀少、作品不易确认,且在今日云南已难觅当年遗存遗迹,此前的探讨不够细密深入,云南雕漆的问题一直扑朔迷离、难以澄清,就明代漆艺乃至工艺美术研究而言,不得不说是个遗憾。本文即着眼于这一研究薄弱之处,试图通过缕析核心文献,结合相关作品,进一步揭示云南雕漆的历史面貌,并期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一、文献再检视
已知直接述及云南雕漆的文献集中于元明时代的鉴藏类著述,今见最早的介绍出自王佐(主要活动于15世纪上中叶)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
剔红器皿,无新旧,但看朱厚色鲜,红润坚重者为好,剔剑环香草者尤佳。……今云南大理府人,专工作此,然伪者多。南京贵戚多有此物,有一等通朱红,有一等带黑色,好者绝高,伪者亦多,宜仔细辨之。[1]
假剔红,用灰团起,外用朱漆漆之,故曰堆红,但作剑环及香草者多,不甚值钱。又曰罩红,今云南大理府多有之。[2]
王佐校增曹昭(活跃于元末明初)《格古要论》,起于明景泰七年(1456)四月,迄于同年七月,后在天顺三年(1459)付梓,以上记述反映的最可能是明代前期情形。文中说,云南大理府人善造剔红,但其中假的不少,假剔红用灰团起堆花,常饰剑环、香草纹样,价格低廉,而据原文标题,假剔红即“堆红”。
到弘治(1488-1505)末年,宋诩(约活动于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上半叶)关于云南漆器品种、纹样的说法出现几点变化:
雕漆。云南造,多花草,有棱角,无剑环,不及剔红黑者浑厚圆滑。……
累漆。云南作,似滑地西皮,其漆乃煮过者为之,器亦坚固。今徽州以漆面为花,制尤坚久。一种堆红者,则累漆之赝也。[3]
宋诩仍说云南造“雕漆”,但纹样无剑环,且提到了作品多棱角、不浑厚,已知的材料里,这是首次,只是他将雕漆与剔红、剔黑并列,认识与今天不同。下条又记,云南也造累漆,而堆红是累漆之赝,这与《新增格古要论》堆红是假剔红之说抵牾。
到晚明,高濂(约活动于嘉靖至万历间,即1522-1620年前后)对明代云南雕漆风貌的描述更加丰富具体:
……(雕漆)民间亦有造者,用黑居多,工致精美,但几架、盘、盒、春撞各物有之,若四五寸香盒以至寸许者绝少。云南以此为业,奈用刀不善藏锋,又不磨熟棱角,雕法虽细,用漆不坚,旧者尚有可取,今则不足观矣。有伪造者,矾朱堆起雕镂,以朱漆盖覆二次,用愚隶家,不可不辩。……[4]
高濂称云南剔红不善藏锋、不磨熟棱角,与宋诩的描述一致,此外又补充说“雕法虽细,用漆不坚”。他也提及伪造的剔红,由所述工艺推敲,当与《新增格古要论》相合。
在品种、风格之外,晚明的沈德符(1578-1642)在云南漆艺史的梳理上有所贡献: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则本朝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间所谓果园厂者,其价几与宋埒,间有漆光暗而刻文拙者,众口贱之,谓为旧云南,其值不过十之一二耳。一日,偶与诸骨董家谈及剔红香盒,俱津津执是说,辨难蜂起。予曰:总之皆云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国破成都,尽掳百工以去,由是云南漆织诸技,甲于天下。唐末复通中国,至南汉刘氏与通婚姻,始渐得滇物。元时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国初收为郡县,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供用库诸役皆其子孙也。其后渐以销灭,嘉靖间又敕云南拣选送京应用,若得旧云南,又加果园厂数倍矣。诸骨董默不能对。[5]
据沈氏所言,云南漆作兴起的基础,是唐代中叶大理国破成都后掳掠的百工。持相似观点的另有李日华(1565-1635),他说,“髹剔银铜,雕钿诸器,滇南者最佳”,认为这固然有“地饶精铁、沙石、玑贝,易于缀饰”的原因,更要紧的在于“唐时酋王阁罗凤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归,流传有法”[6]。关于云南漆作的肇始,这是两份珍贵的意见。而对本文,沈德符有关元明时代的缕述更有意义:明代云南平定,当地漆工进入内府,服务宫廷,此后逐渐消亡,嘉靖间(1522-1566)又命云南拣选送用。他还提到,当时有些古董家对云南雕漆的印象大致是漆光暗淡、刻纹朴拙。
二、年代、品种与风貌考辨
讨论明代的云南漆器,以上几则材料最为关键,在另外一些文献,如王三聘(1501-1577)《古今事物考》,刘侗(1593-1636)、于奕正(1597-1636)《帝京景物略》,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中,也能见到与之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字,但它们当系承袭抄录,实际并无新意、乏善可陈。上引材料提供的知识已经不少,但说法有时很模棱,意见有时不统一,与遗存的实物也不能完满对证。若结合其他材料,则以下几个问题还可继续探讨。
1. 年代
沈德符说,云南漆工明初布满内府,嵇若昕循此记载,经由表征分析,指出山东邹城明鲁荒王朱檀(1370-1390)墓出土的剔黄笔管应系明初滇工之作[7]。推测即使属实,此例也为孤证,云南派漆作在明初的发展脉络仍然太过朦胧。相比之下,如今对于明中期的知识稍多,关于曾任职云南的官员应履平(?-1453)的一段记载至为珍贵:
应履平,字锡祥,奉化人。……升贵州按察使,奉敕同兵部尚书王骥、平蛮将军蒋福帅师征麓川,有功,升云南左布政使。时有太监奉命监造剔漆器皿进用,供费百出,民不能堪。平谂其将讫工,别造私物,密疏钦造数完,或且止,或加造,奉旨:“毕造,起送部”。檄至,履平怀之,中道驰入,太监怒叱之,对曰:“奉旨,请回京”,出文以视,遂解一方倒悬。……[8]
“剔漆”显系雕漆。按《明英宗实录》,应履平升任云南左布政使在正统三年(1438)七月[9],则在此之前,云南已有太监在奉命监造雕漆进用。北京与云南之间,千里迢迢,跋涉艰险,器用传办、送交实在不易。联系沈德符的说法,依常理推想,倘若宫中仍有云南漆工,则应该不必去当地造办,倘若宫中曾有云南漆工,则到此时恐怕已消亡殆尽。另外还可注意的是,英宗皇帝(1436-1449[年号正统]、1457-1464[年号天顺]在位)年少登极,到正统三年,也不过十二岁,在位之初,太皇太后张氏临朝,“三杨”等勋旧辅政,朝野尚称清晏,且按照当年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品格,造作的旨令如经外朝传下,一定会遭到极力的劝阻。对于此事,最易产生的推测有两个。一是它系此前宣德年间的遗留。但在明代,每逢新帝即位,总要与民更始,即位诏中,循例要下令停止各项采办和造作,若有监督内官,也要从速回京。宣德时派造而正统初未停,以及停后重启,现在都没有史料证明。另一个推测是,这确实是正统朝派下的造作,不过它并非出自外朝动议,而是源于内府的主张,或者是由内府径直将旨意传达到地方。在明代中期,这类操作有事例可寻。
弘治五年(1492),宫中命陕、甘二处织造彩妆绒毼曳撒数百事,引来了监察官员的谏阻,依奏议所言,旨令的下达系由司礼监传写帖子,而外朝的工部未曾经手。文中还推测,皇帝之所以这样操作,可能是因为心有不安[10]。尽管这则记载的时间较晚,但仍有参考价值,正统初年令云南供用雕漆器皿,或许也是有此心理、走的这条路径。于此,还可考虑的是正统朝司礼监的一个重要执掌者及其与英宗皇帝的密切关系。此人就是明代几个擅权干政的大宦官之一——王振(?-1449),英宗即位后,他即掌领司礼监,由于为人黠慧、曾经陪侍青宫,很受皇帝信重。后来的跋扈乖张在早期即有迹象,以至于他险些被太皇太后处死,罪名就是“侍皇帝多不法”[11]。在不法的诸事里,或许就有鼓动年少的皇帝,乱开艰难的造作。
既然云南还能承接派造,则当地民间的漆作此前应有不小的能力,之后,也可能长期维持,弘治三年(1490)八月间的一则奏陈隐约透露了这样的讯息:
巡抚云南都御史王诏等奏:故镇守太监王举,不遵诏例,造作奇玩器物额外进贡,请以其物之重大难致,如屏风石床之类,发本处库藏收贮,金银器皿镕化之,与宝石、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户、工二部备用,其寄养象只,堪充仪卫者解京,不堪者付与近边土官,令出马以给驿递。得旨:并解送来京。[12]
王举镇守云南,他造来进贡的漆器相信就是产在当地,很可能包含雕漆。由时代稍前的这些材料分析,沈德符所言嘉靖时云南又受命遣送工匠,大概是实。
2. 品种


图1 明中期 滇南王松造
剔红文会图方形委角盘
故宫博物院藏
图2 明弘治 尹禄造
剔黑花鸟大盘
原日本私人藏
取自保利艺术博物馆编:
《宋元明清漆器特展》,页69
几条文献都说,云南造雕漆,这无可怀疑,出自滇工之手的剔红现在还有保存,学界多已熟知,即北京故宫博物院那面“滇南王松造”的文会图方盘。(图1)上引文献还几次提到云南多作摹仿剔红的堆红、罩红,做法是以矾朱、灰团堆起花纹,然后罩漆。《髹饰录》对堆红工艺的记述与此大同小异,王世襄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剔红表里一致,堆红则里外用料不同,剔红刻后刀法尽在,堆红则刻后罩漆,花纹不免臃肿,较难生动流畅[13]。按宋诩和高濂的文意,云南雕漆起码还包括剔黑。而今,相信为滇工作品的剔黑也有披露,如原为日本私人收藏的一面花鸟纹圆盘,其边缘有刻铭“弘治年滇南尹禄造”[14]。(图2)据悉,藏于日本的明代剔黑中,还有些未退光、未打磨、外底较粗糙的作品,它们被通称为“云南雕”[15]。名称容易令人将之视为云南雕漆,但事实如何,仍然成谜。
《宋氏家规部》称,云南所造的累漆近似“滑地西皮”,这说的该是花纹效果。在同卷中,恰也记载了滑地西皮,说“花底如仰瓦光泽,而且坚薄不露素地”。但这个解释并非原创,它的源头应在曹昭:
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为贵,底如仰瓦,光泽而坚薄,其色如胶枣色,俗谓之枣儿犀,亦有剔深峻者,次之。……[16]
可见,《宋氏家规部》所称滑地西皮,实为这里描述的剔犀。由此,依宋诩所说,累漆面貌即近于剔犀。又,“累”与“堆”意义接近,《髹饰录》对堆漆有记述。按杨明的注解,堆漆有复色之法,指花纹用漆分几次堆成,每次更换漆色,完成后花纹侧面露出有规律的不同色层,很像剔犀。这又正与累漆近似剔犀的说法呼应,看来,累漆极可能就是堆漆。但宋诩还说,堆红是累漆之赝,在此,他区分真赝的标准想来当与王佐一样,也是用料,累漆堆花全用漆,而堆红里用漆灰、在外罩漆。
3. 风貌
作为明代重要的鉴藏著作,《燕闲清赏笺》的意见影响颇大,它对云南剔红风格的形容曾被数次转抄。相信就是受了这些文献的引导,以前见到特征如上述的明代雕漆,专家常常会将它与云南作品联系,不善藏锋、用漆不坚,俨然云南雕漆的判定标准。
但明代的云南雕漆应当不只有这种面貌,“滇南王松造”剔红文会图方盘就恰好是个证据。王世襄先生早已指出,这只方盘的刀法实属圆润一路,风格与宣德朝作品相似,盘边花卉更是明代早期的做法。由此即知,明代云南雕漆的风貌并不单一,也有明人推重的刀法圆润的一类。沈德符也认为,“若得旧云南”,可“加果园厂数倍”,依照文意,“旧云南”当系嘉靖间再募滇工以前,即明代早中期的产品。而专家此前正相信,剔红文会图方盘的年代应在明中期。总之,云南雕漆应受过嘉兴派的影响,有些作品的风格属圆润浑厚,在晚明,它们尚能得到文士的认可。按《宋氏家规部》,至迟到其成书的弘治末年,不善藏锋已成为明人眼中云南雕漆工艺的突出特点。或许在此后的发展中,云南雕漆更多采用新的刀法,终使爽利之风后来居上,圆润一路退出主流。当然,还该说清,尽管这面文会图方盘确属滇工制作,雕刻圆润浑厚,但它终归是个孤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对其价值,不宜过高估计。

图3 剔黑花鸟大盘局部
取自保利艺术博物馆编:
《宋元明清漆器特展》,页71
对于认识明代云南雕漆的主流风格,上引近年发表的“弘治年滇南尹禄造”剔黑圆盘相信颇有意义。此盘在红漆地上满雕黑漆纹样,题材为菊花、莲花、石榴花、栀子花和飞旋、栖息的鸟雀,鸟雀形象甚不醒目,这些花卉是绝对的主体。专家先前已指出,它的漆层较薄,纹饰细部多采用斜刀阴刻,线条流畅缜密而快利。(图3)比这更易觉察的是,其花纹繁满细碎,和元明时代嘉兴派的圆润浑厚迥异,而与高濂所言云南的雕法之“细”契合。在沈德符的时代,古董家们非常推重永乐、宣德间嘉兴派主导下的官府雕漆,对被认作旧云南的那些则“众口贱之”,也可见两类作品风貌必然不同。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文中已经提到云南的“漆光暗而刻文拙”。剔黑圆盘的雕刻其实颇精细考究,难以纳入拙的行列,但它满密细碎的装饰面貌毕竟与永、宣时代的作品有别,不合于古董家倾心的圆润浑厚,在中晚明,这个特点或许也曾成为时人眼中云南雕漆的短处,令它们不被爱重。

图4 明中期 剔红飞龙纹圆盒
故宫博物院藏

图5 明中期
剔红穿花龙纹双耳扁瓶
故宫博物院藏

图6 明中期 剔红松竹梅草虫纹圆盒
故宫博物院藏
“弘治年滇南尹禄造”剔黑圆盘或能成为可资比照的标准器,用来分辨可能属于云南一派的雕漆。因为缺乏可靠的实物对照,以往学者尽管会推测那些用刀露锋、纹带棱角的明代雕漆为云南作品,但有时仍要慎重地表示,证据不足,尚待查考。这类器物的典型可举北京故宫旧藏的一组剔红,包括碗、盘、盒(图4)、扁瓶(图5),主题纹样有松竹梅、双龙、双翼龙、双螭、双狮、四狮、盘长灵芝等。一些辅纹非常特殊,如其中一件松竹梅盒上,点缀着蜂、蝶、螳螂、蛙、蜥蜴(图6),它们极少见于明代官府雕漆,专家称具有民间乡土趣味[17]。前人已注意到这组剔红的刀不藏锋与文献相符,而其繁密的构图、板平的纹样与这面剔黑圆盘近似,颇能左证它们产在云南,或出于云南漆工之手。


图7 明中期
剔红缠枝莲纹碗
故宫博物院藏
图8 明中期
剔黄缠枝莲蟠螭纹棋子盒
故宫博物院藏


图9 明中期
剔红岁寒三友图圆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0 明
剔黑岁寒三友图委角方盘
安徽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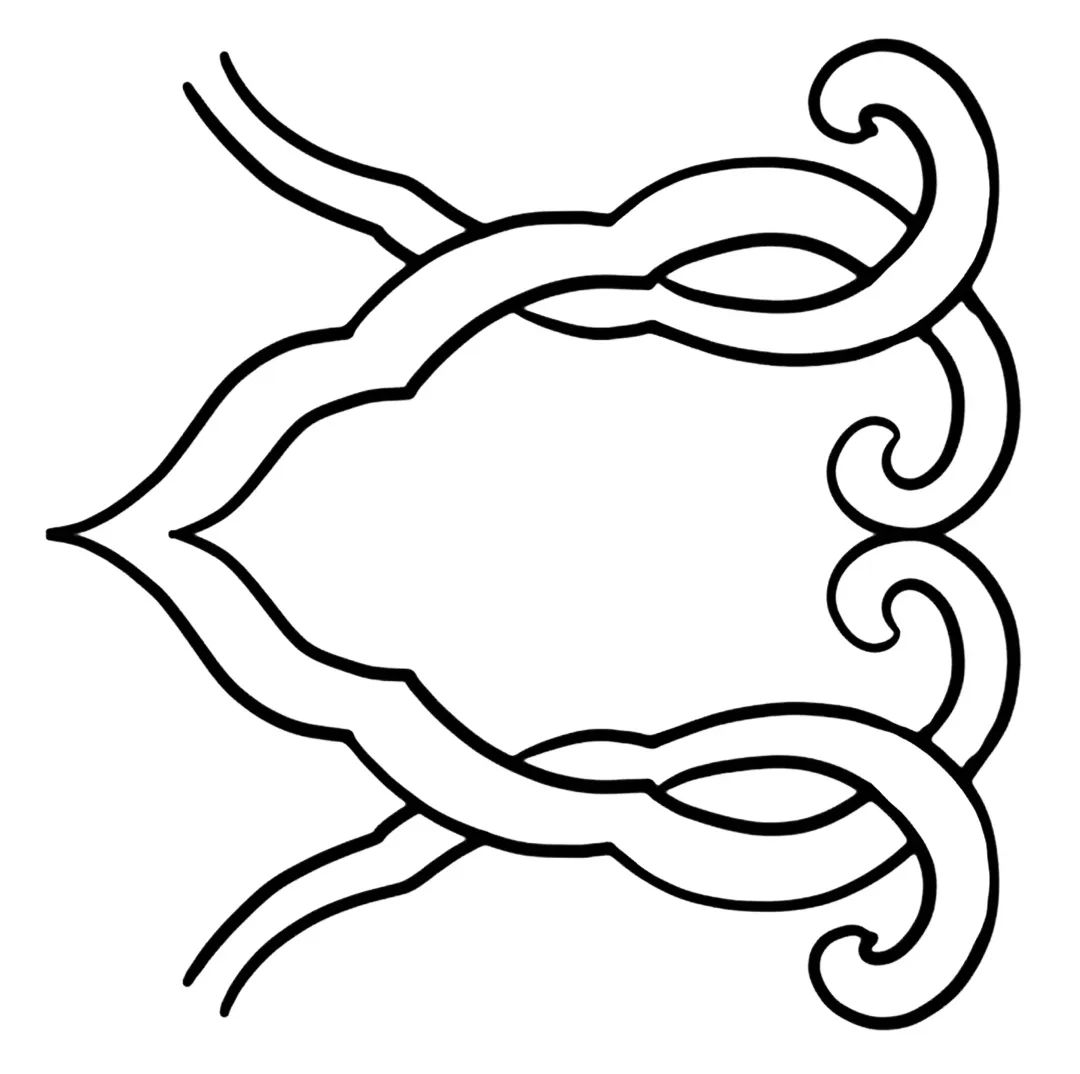
图11 明中晚期
剔红松竹梅委角方盘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12 《营造法式》
(故宫殿本书库钞本)
剑环纹结构摹绘
综合参照这些器物雕饰的技法、构图、题材特征,在已知的明代雕漆中,能进一步推定几件属于云南作品,例如此前曾被专家怀疑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剔黑缠枝莲纹圆盒,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剔红缠枝莲纹碗(图7)、剔黄缠枝莲蟠螭纹棋子盒。(图8)另外,还有国博的剔红岁寒三友图圆盘(图9)、安徽博物院的剔黑岁寒三友图委角方盘(图10),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剔红松竹梅委角方盘(图11),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剔黑牡丹纹圆盒、根津美术馆的剔红狮子牡丹纹圆盒、冈山美术馆的剔红菊花纹圆盒、大和文华馆的剔红麒麟纹长盘[18]等。其中,安徽博物院和大都会博物馆两件方盘的纹样题材、风格与盘沿的竹节式造型竟几乎完全相同,区别大致只在漆色,两者的关系显然特别紧密,不排除有出于同一作坊乃至同一漆工的可能。

图13 南宋 银梅瓶
四川德阳孝泉南宋窖藏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图14 南宋 剔犀菱花形执镜盒残片
福建闽清白樟乡南宋墓出土
福建省闽清县文化馆藏
最后,关于云南雕漆的纹饰面貌,另有一事需稍加申说。王佐记述,云南的假剔红多作剑环、香草纹样,宋诩则称,云南“雕漆”多花草、无剑环。剑环、香草系指线形纹饰,现在大体确定,要说的是剑环原本的形式与概念。王世襄在批注《髹饰录》中“剔犀”一节时,以计成(1582-?)《园冶》所附剑环式圈门的图案,来推测黄成所记的“剑环”样貌,后继学者有时也遵从此说。而在今天的海外学界,被认作“剑环”(pommel scrolls)的纹样,则是中国学人习称的如意云头,这一判断相信得自一些时代较晚的有关中国古兵器的图示,不为无据。然在《髹饰录》原文里,剑环与绦环、重圈、回纹、云钩并举,虽然都应是线形纹饰,但具体样式当有不同。又,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论“香合”时提到,“宋剔合色如珊瑚者为上,古有一剑环、二花草、三人物之说”[19],细推文意,似乎剑环之名由来已久。而在北宋李诫《营造法式》的彩画纹样中,确实早有“剑环”一名。它整体作对称多曲状,一端弯曲斗合,一端聚结出尖(图12),在当下很多学人那里,这种纹样也会被称作如意云头。建筑装饰与工艺美术纹样的相通之处不乏其例,如《营造法式》的彩画纹样就多见于宋辽丝绸,装饰形似剑环纹的银器曾经出土(图13),而纹样相仿的剔犀也已发现了。(图14)看来,剑环纹的本来面目很可能如同《营造法式》所画,只不过到后来,它所指代的纹样或许又有扩展,乃至能够代表线形纹饰,与花草、人物相提并论。
尽管宋诩称云南雕漆无剑环,但他所说的雕漆是与剔红黑器并列的一种,并非今日认为的雕漆,故而不能以此否定王佐的记载。剑环结体简单,雕刻不难,且据文震亨之言,其地位一度很高,而现在遗存的丰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年制作的繁盛,云南雕漆不做剑环似乎不合情理。还该注意,剑环等线形纹饰多用于剔犀,相信云南的雕漆也包含了这一品种。
三、正德款剔红圆屏刻铭献疑

图15 明正德 柴增造 剔红人物楼台图圆屏 上海博物馆藏

图16 剔红人物楼台图圆屏刻铭
带正德纪年铭的漆器,长期以来未闻发表。那面“正德丁卯黄阳柴增造”剔红人物楼台图圆屏(图15)刊布的契机,是上海博物馆2018年11月举办的“千文万华——中国历代漆器艺术”展览。刻铭的文字为博物馆专家释读,由图片分辨,“正德丁卯”“阳”“柴增造”八字较为清晰,没有疑义,但“黄”字有所模糊,准确与否,还有商榷的余地。(图16)
参照其他明代雕漆上的刻铭,如“平凉王铭”“平凉王琰”“滇南王松”来看,工匠署名之中的籍贯,一般是府级或以上。然检索明代地方行政区划,非但黄阳府遍寻不到,在更低层级的单位中,也没有符合的地方。故对“黄”字的认读,或许有误。此字更可能是“贵”,在字形上,它与图片所示亦非常相像。而《万历贵州通志》所载贵阳府的“方产”之中,明确记有“雕漆器”[20]。虽然这则文献的时代较晚,但工艺品种极少骤然出现,况且,依方志所载,雕漆造作在贵州并不罕见,说明它在当地应有些传统,故藉以推断正德前后贵阳等地出产雕漆,或出过雕漆工匠,应该合情入理。所以,判断那位柴增出自贵阳并非臆测。而且,从刊布的图片观察,这面圆盘的漆色不甚红亮,较为暗淡,与晚明古董家眼中云南雕漆“漆光暗”的特点似可对应。贵州与云南毗邻,雕漆风格相信会受其影响,柴增甚至有可能也属滇工一派。但话说回来,以上只是一种质疑和猜测,铭文究竟是作“黄阳”还是“贵阳”,尚待方家再予严谨的辨析与求证。
尾语
在以上讨论当中,先行检视的几则文献很受倚重,它们成为考证、分析的基础。文献固然珍贵,但局限在所难免,比如鉴藏类书籍的作者不见得熟悉工艺,王佐和宋诩关于假剔红的认识就产生了分歧。对于倚重这类文献的危险,本文并非全无意识,之所以仍如此展开,则多缘于史料稀少的无奈。文中依据刻铭器物风格,区辨疑似云南雕漆作品,亦嫌说服力度不足,尚且只能作为猜测。另外,海内外的公私收藏一时难以搜罗齐全,以上援引的实物还不甚丰富,加之笔者不曾从事工艺制作,也没有机会上手观摩作品,因而对于实物缺乏直观认识,写作仅能藉助文献记载和实物图像,解说的深度当然难与漆艺工作者和文博机构学人相比。总之,限于资料和学力,本文的论述一定不免偏颇,甚至多有错漏。
云南雕漆的问题已困扰学界有年,期待新研究的推出,令其历史面貌更加清晰,也渴盼新材料的发现,能从根本上解答关于它的众多困惑。
注释:
[1]( 明)曹昭编着、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论》(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据清光绪间李锡龄辑刻《惜荫轩丛书》本),卷8,〈古漆器论·剔红(后增)〉,页257。
[2](明)曹昭编着、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论》,卷8,〈古漆器论·堆红(后增)〉,页257。[3](明)宋诩,《宋氏家规部》,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据明刻本影印),卷4,〈整备簿籍·长物簿·漆类〉,页48。[4](明)高濂,《燕闲清赏笺》(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据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雅尚斋刻本),上卷,〈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页66-67。[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据清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刻本),卷26,〈玩具·云南雕漆〉,页661-662。[6](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据民国有正书局石印本),卷3,页291-292。[7]嵇若昕,〈明初滇工雕漆工艺〉,《故宫文物月刊》,425期(2018.8),页96-105。[8](明)周希哲修,张时彻纂,《嘉靖宁波府志》(早稻田大学藏,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卷27,〈列传二·应履平〉,页37b-38b。嵇若昕先生前曾留意此则材料,并以之简论云南雕漆贡品,见嵇若昕,〈明初滇工雕漆工艺〉,页105。[9](明)孙继宗监修,陈文、彭时总裁,《明英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据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影印),卷44,〈正统三年七月丙戌〉,页851。[10](明)张懋监修,李东阳、焦芳、杨廷和总裁,《明孝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据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影印),卷60,《弘治五年二月庚午》,页1159-1160。[11](清)万斯同,《明史》,收入《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2005,据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卷405,〈宦官传·王振〉,页4995。[12](明)张懋监修,李东阳、焦芳、杨廷和总裁,《明孝宗实录》,卷41,〈弘治三年八月庚子〉,页860。[13](明)黄成撰,杨明注,王世襄解说,《髹饰录解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据民国十六年紫江朱氏刊本),页129。[14]保利艺术博物馆编,《宋元明清漆器特展》(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2012),页68-71。[15]李经泽,〈剔黑器概述〉,《中国生漆》,2016年3期,页13-21。[16](明)曹昭编着、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论》,卷8,〈古漆器论·古犀毗〉,页256。[17]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雕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页265。[18]德川美术馆、根津美术馆编,《彫漆》(名古屋:德川美术馆、东京:根津美术馆出版,1984),页81图版111,页82图版112,页127图版181、182,页296、307、308图版目录。[19](明)文震亨,《长物志》(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据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铅字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卷7,《器具·香合》,页97。[20](明)王来贤,陈尚象修纂,《万历贵州通志》,收入《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据日本东京尊经阁藏明万历刻本影印),册18,卷3,〈贵阳府·方产〉,页64。
本文原刊《故宫文物月刊》463期(2021-10),此次刊发时略有改动。
图、文来源:工艺美术理论专委会公众号